注意:本文最后更新于 2024年4月15日,若文章包含具有时效性内容,请自行测试或联系作者!
作者简介:尤金·保罗·维格纳(Eugene Paul Wigner,1902年11月17日 -1995年1月1日)是一位匈牙利裔美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因其在原子核理论、量子力学的对称性原理,以及量子力学在化学和核子物理中的应用方面的贡献而闻名。1963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两位昔日高中同窗聊起彼此的工作。其中一人成了统计学家,正专研人口趋势。他把一篇论文拿给老同学看,这篇论文按惯例从高斯分布开始说起,统计学家向老同学解释用于实际人口数、平均人口数等等的符号意涵。老同学显得有些迟疑,不太确定这位统计学家是否在唬弄他。他问说:「你怎么知道是那样?那这边这个符号是什么?」。统计学家说:「噢,这是π。」「π是什么?」「圆的周长对直径的比率。」老同学说:「哇,你玩笑开得太过头了,人口怎么会跟圆周长有关系!」
我们很自然的会莞尔于这位老同学思路的单纯。然而我必须承认,当听到这个故事时,我心中油然生起异样之感,因为故事中这位同学的反应,流露的不过是直白的常理。但更让我纳闷的是,后来没过多久有人找我讨论一个疑惑【注:此人是当时就读于普林斯顿的维纳(F. Werner)】,亦即当我们测试理论时,只选用了很小范围的数据。他说:「如果我们建构理论时,根据的是现在忽略的现象,并且忽略一些现在关注的现象,我们怎么知道会不会建构出与现在理论大相迳庭、但对现象却有同等解释效力的另一理论?」的确要承认,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判定不会有这样的理论。
以上两个故事呈显了两个重点,亦即这篇论文的主题。首先,数学概念在全然意料外的脉络中出现,而且通常很出乎意料的,能够缜密且精确的描述这方面的现象。其次,正因为这种状况,也因为我们不理解数学如此有用的个中缘由,我们无法知道一个用数学概念表述的理论是否唯一合适的理论。我们的状况就像是手里握着一串钥匙、需要连续打开数道门的人,当他总是试一、两次就找对钥匙,不免开始怀疑钥匙与门锁之间是否有唯一的对应关系。
以下要说的大部分并无新意,大多数科学家可能都曾以某种方式想到过。我的主要目的是从几个面向去阐明。第一,数学在自然科学中巨大的有用性几近神秘,找不出合理解释;第二,正是数学概念如此不可思议的有用性,促使我们注意物理理论唯一性的问题。为了建立第一个论点,亦即数学在物理学中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有必要先谈谈「什么是数学?」接著再谈谈「什么是物理学?」然后再谈谈数学如何跨入物理理论,最后则是,数学在物理学中角色的成功为何如此令人费解。关于第二点,物理理论的唯一性,在此将不多着墨。要想对这问题给出适切的答案,还需要进行周密的实验性与理论性研究,而这类研究目前还未展开。
数学是什么?
曾有人说哲学是为了要滥用而发明的术语【注:引自杜比斯列夫(W. Dubislav)之《当代数学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Mathematik in der Gegenwart)(1932)】。沿此脉络,我会说数学是为了有技巧的运用概念与规则而发明的科学;主要强调的是概念的发明。如果数学定理都必须出自公理中已出现的概念,那么有趣的数学定理很快就会告罄。再者,虽说初等数学,尤其是初等几何的建构,无疑是为了要描述真实世界的对象,但是更高等的数学概念则未必如此,尤其是那些在物理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数学概念。准此,整数对的运算规则,显然是被设计成与分数运算的结果相同,即使我们初学分数时并未提到「数对」。用于数列的运算规则则对应到无理数,这个运算仍然隶属于重现已知的数量运算规则的范畴。然而大部分更高深的数学概念,诸如复数、代数、线性算子、伯瑞尔集合(Borel sets)——类似例子是无穷无尽的——则是数学家设想出来,以做为展现其巧思与形式美感的主题。事实上,数学家定义这些概念时,即已知道可对其运用有趣且精妙的构思,这正是数学家深具巧思的首要明证。创造数学概念所需的思考深度,则可展现在日后运用这些概念之技巧需求。伟大的数学家堪堪走在容许的界限上,在可行的范围内充分且近乎果决的尽情驰骋。然而这样奔放的思路并未让他们陷入矛盾的困境,光这件事本身就是奇迹。我们很难相信单凭达尔文的天择过程,人类的推理能力即可演化到如此完美的程度。然而,这并不是我们目前要谈的主题。在此强调,而且后面还要重温的重点是,数学家若未定义公理之外的概念,则他仅能建立起寥寥可数的有趣定理;而数学家之所以定义这些公理之外的概念,则是着眼于能对它们运用巧妙的逻辑运算,使得运算本身以及由此可得的普遍性与简洁性,都可满足我们的美感【注:博兰尼在其《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1958)中曾说:「所有的这些困难不过是由于我们拒绝去明白,若不承认数学最明显的特征即它很有趣,则数学便无法定义。」(188页)】。
复数便是一个显例。当然,我们的经验不需要导入这些数学量。事实上,若要数学家提出研究复数的正当理由,他必会义正词严地指出在方程式论、级数论、乃至一般解析函数论中的许多优美定理,这些都根源于复数的引入。数学家绝不愿放弃研究这些由他们巧思所创造出的优美成就【注:在此脉络下,读者也许会想知道希尔伯特对直觉主义相当不耐的评语,他说直觉主义「旨在破坏与丑化数学。」 参见〈数学的新基础〉(Neubegründung der Mathematik,Abh. Math. Sem. Univ. Hamburg I (1922) ,157页);或其《个人全集》(Gesammelte Werke (1932),Springer,188页)】。
物理是什么?
物理学家志在发现物理世界的定律。为了理解这一陈述,有必要先分析「自然律」的概念。
围绕着我们的世界复杂难解,最明显的例证便是我们无法预测未来。虽然世人总笑说只有乐观主义者才会认为未来不可确定,但乐观主义者在此是对的:未来的确不可预料。正如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曾评论的,在如此复杂难解之世界中的一项奇迹是,我们居然能从事件中找出某些规律。伽利略所发现的一项规律是,如果两个石头同时自等高处落下,将会同时着地。自然律即是关于这些规律性。伽利略发现的规律是一大类规律的原型。这样的规律因为下列三个理由而令人惊讶。
第一个理由是,它不仅在伽利略的时代、在比萨成立,而且在地球上的任一处都成立,不仅过去成立、现在成立,而且未来也将永远成立。规律的这项特质被称为不变性,正如我先前曾指出的,若没有类似于从上述伽利略的观察所推广出的不变性原理,物理学将无法存在。第二个惊人的特质是,我们所讨论的规律性不受许多情境因素影响,不管是否下雨、无论实验地点是室内或是比萨斜塔、无论放开石头的人是男是女,这项规律都成立。甚至是不同的两个人从相同高度同时各放开一颗石头,这项规律也仍旧成立。很明显,无数的其他条件都不会影响伽利略规律的有效性。有如此多可能影响观测现象的情境,结果却无关紧要,这也是一种不变性。然而这种不变性的性质迥异于前一种,因为它无法被表达成一条通则。探讨能影响或不能影响现象的各项条件,是每个领域早期实验探索的一部分,这需要实验者的技巧与创见,让他得以证明现象只被相对少数的一些相对容易实施与复制的条件所决定【注: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多伊区(M. Deutsch)生动的文章,见 Daedalus 87(1958),86页。承西蒙尼(A. Shimony)告知普尔斯有一段相似的话,参见〈科学哲学文集〉(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57),The Liberal Arts Press,237页)】。在本例中,伽利略将他的观察限制在相对较重的物体,便是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步。再强调一次,若不是有些现象只会被我们可应付的少数条件所影响,物理学将不可能存在。
上述两点,虽然从哲学家观点来看意义深远,却并非最让伽利略吃惊之处,而且这两者也未包含特定的自然律。自然律存在于这样的陈述:一个重物从给定的高度落下所需的时间,与该落体之大小、材质及形状无关。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框架下,此陈述等于是说,作用于自由落体上的地心引力与该落体之质量成正比,而与该落体之大小、材质及形状无关。
以上的讨论旨在提醒诸位,首先,「自然律」的存在一点也不自然,更别提能够被人类发现【注:薛定谔在其《什么是生命》(What is Life)提及这第二个奇迹可能超出人类的理解】。笔者便曾呼吁要重视「自然律」相继的各个层次,每一层都包含比上一层更普遍、包罗更广的规律,发现下一层会使我们较诸先前更能深刻地洞察宇宙的结构。然而,目前脉络下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这些自然律,即使虑及它们最广泛的成果,也只构成我们对于物理世界知识的一小部分。所有的自然律皆是条件式述句,容许我们根据现在的知识,预测某些未来的事件。而且从预测的观点而言,现在状态的某些面向(其实是决定世界现状的绝大多数因素)都是不相关的。这里所说的无关性,指的是前面讨论伽利略定理时的第二点【注:笔者确信无需再指出,文中所提及之伽利略的定理,并未涵盖伽利略对自由落体定律的所有观察】。
关于世界的现状,诸如我们生活所在的与伽利略进行实验的地球、太阳与所有周遭环境的存在,自然律完全不置一词。与此相呼应的是,首先,自然律只在特殊条件下—当世界现状的所有相关决定因素已知时—才能用来预测未来事件。另一与此相呼应的是,物理学家能够建造出可预见其功能的机器,这构成他们最卓越的成就。物理学家在这些机器中,创造出一种所有相关要素均为已知的环境,因此可以预测机器的行为。雷达与核子反应炉即是这类机器的范例。
前述讨论的主要目的在指出,一切自然律皆系条件式述句,且其仅与人类对于世界所知的极小一部分相关。因此,古典力学做为最广为人知的物理理论原型,是在物体的位置等资料已知时,给出物体位置坐标的二阶导数。而对于物体的存在与否、目前所在或其速度等,则毫无着墨。为求精确,我还得提醒各位,约在30年前我们已得知即使是条件式的陈述,也无法完全精确:条件式的陈述其实是机率规则,让我们能根据对现状的所知,智性的猜测物理世界的未来性质。自然律无法让我们建构绝对性的陈述,甚至对世界现状的绝对性条件陈述都做不到。「自然律」的机率本质也可在机器上显现,至少在核反应炉的例子是这样,如果用极低的能量去运转反应炉的话,即可得到验证。然而,基于机率本质对于自然律所额外增加之局限【注:可见如薛定谔,uber Indeterlninismus in der Physik,J. A. Barth,Leipzig,1932。】,下文将不再着墨。
数学在物理理论中的角色
在复习过数学与物理的本质之后,我们就能更适切地重新审视数学在物理理论中的角色。
我们在日常的物理学中,会运用数学计算自然律的结果,将条件式陈述应用到最有可能或是我们感兴趣的特定条件上。为了这么做,自然律必须以数学语言表示。然而计算既有理论的结果并非数学在物理学中最重要的角色。数学或说是应用数学,在此功用下并不是此情境的要角,不过是工具罢了。
然而,数学的确也在物理学中扮演了更具主导性的角色。我们在讨论应用数学时曾提到,自然律必须先以数学语言来表述,才能成为应用数学的对象,这句话其实已暗示了数学更重要的地位。自然律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说法,早在300年前即已出现【注:出自伽利略】;这句话在现在比以往更正确。为显示数学概念在建构物理定律时的重要性,试回想量子力学的公理,它是由大数学家冯诺曼(John von Neumann)明确地建立,或由大物理学家狄拉克(Paul Dirac)隐含地提出的。量子力学有两个基本概念:态(states)与可观测量(observables)。态是希尔伯特空间(Hilbert space)的向量,可观测量则是作用于这些向量的自伴算子(self-adjoint operators),而可能的观测值则是这些算子的特征值。但我们最好就此打住,免得变成条列线性算子理论的种种数学概念。当然,物理学的确只选择某些数学概念来建构自然律,且仅用到其中一小部分。数学概念的选择当然也不是从数学名词表单上随便选的,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有许多情形是物理学家独立发展出这些概念,然后才认知到此前数学家就已酝酿出来了。然而并非像常说的那样,以为数学使用最简洁的概念,因此不管使用何种形式系统,都会用到数学概念。我们已经看到,数学概念的选择并非出自简洁性(即使是数对构成的数列也远非最简单的概念),而是因为它们适于进行巧妙的运算,以及独特、卓越的论证。别忘了量子力学的希尔伯特空间是具备厄米特纯量积(Hermitean scalar product)的复希尔伯特空间。对于非专业者,复数既不自然也不简洁,且也无法从物理观察中找到暗示。此外,复数在此的运用并不是应用数学的计算技巧,基本上反而是表述量子力学形式系统的必须要件。最后,从目前的趋势看来,不仅仅是数,而且所谓的解析函数也会在量子论的表述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此我指的是快速发展的色散关系理论(theory of dispersion relations)。
我们很难不觉得,我们所面对的是一项奇迹,它的神奇并不亚于人类心灵能将数以千计的论证联缀起来而不自相矛盾。它也可与另两项奇迹相比拟:一个是自然律的存在,另一个是人类心灵居然有能力去发现自然律。就我所知,最能贴切解释数学概念出现在物理学的,是爱因斯坦的说法:唯有优美的理论,才是我们能够欣然接受的物理学理论。需要运用大量智力的数学概念,是否具有美感,这一点还有待讨论。然而,爱因斯坦的观察顶多能解释我们乐于接受那些理论,但未触及理论内在的精确性。因此,我们将转而讨论后面这个问题。
物理理论的成功真的值得惊奇吗?
物理学家把自然律写成数学形式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是因为他不太负责任。当物理学家发现两个量之间的连结与数学中众所周知的某种连结关系相像时,他便遽下结论,认为这个连结即是数学所讨论的连结,而这不过是因为他不知道是否有其他类似连结罢了。现在讨论的目的,不是要驳斥物理学家不太负责任的说法。也许他真是如此。然而,在此得强调,有数不清的例子是当物理学家把粗糙的经验用数学表述后,便能够对一大类的现象做出极度精确的描述。这显示数学语言之所以值得赞赏,并不在于我们只会说这种语言;而是在很真实的意义上,显示了数学就是正确的语言。让我们看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常被引用的行星运动。透过主要在意大利进行的诸多实验,自由落体定律当时已是相当确立的定律。以今日的精确标准来衡量,这些实验不可能非常精确。部分原因来自空气阻力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当时还无法测量极短的时间间隔。无论如何,藉由这些研究,意大利的自然科学家熟悉了物体在大气中的运动。而后牛顿将自由落体定律与月球的运行联系起来,他注意到在地球上投掷石块的抛物线轨迹,以及月球在天空中的圆形轨道,都是数学上椭圆的特例。于是他根据单一的、在当时看来非常近似的数值巧合,从而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想法。从哲学观点来看,牛顿所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对他的时代以及他本人都是难以接受的。从经验观点来看,它所依据的观测寥寥可数。他用来表述的数学语言包含了二阶导数的概念。曾画过曲线密切圆(osculating circle)的人都知道,二阶导数并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概念。牛顿勉强建立的万有引力定律,他自己仅能验证到4%的精确度,但现在已被证明其误差小于百万分之一。这几乎可被视为绝对精确了,直到最近物理学家才又大胆地研究起其精确度的限度【注:诸如狄克(R. H. Dicke) American Scientist,47(1959),25页】。当要谈起用数学家看来很简单的形式所表达、但其精确度超出所有合理预期的自然律,屡屡被引述的牛顿定律当然是第一个被提起的典范。让我们再就此例扼要重述一次我们的论点:首先,这一定律,特别是其中出现的二阶导数,只对数学家是简单明了的,从大众常识的角度或对不具数学倾向的新手而言,它并不简单。第二,它是在非常有限范围内的条件式定律。它对吸引伽利略石块的地球没给出任何解释,也没说明月球的轨道为何是圆形,同样也没阐明太阳系的其他行星情况。这些初始条件留待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去解释,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第二个例子是普通、初等的量子力学。它源于波恩(Max Born)注意到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提出的一些运算规则,形式上与数学家早已确立的矩阵运算规则完全一致。从而波恩、约当(Pascual Jordan)和海森堡提议用矩阵代替古典力学方程中的位置变数和动量变数。他们把矩阵力学的法则运用到几个高度理想化的问题,结果相当令人满意。然而,当时并没有理性的证据可以证明,在更实际的条件下他们的矩阵力学也是正确的。的确,连他们也是说「这裡建议的力学在基本特质上应该算是正确的」。事实上,他们的力学首次应用至实际问题,是数月后由包立(Wolfgang Pauli)对氢原子所做之研究,结果与经验一致。这虽令人满意,但也还可以理解。因为海森堡的计算规则就是从包括氢原子旧理论在内的问题抽象出来的。只有到了将矩阵力学或与之数学等价的理论用到海森堡的计算规则并无意义的问题时,才出现了奇迹。海森堡的规则预设古典运动方程的解具有某种周期性,但氦原子中两个电子的运动方程,或者更重的原子里为数更多的电子运动方程,根本不存在这种性质,因此海森堡的规则不适用于这些情况。然而就在数个月前,康乃尔大学的木下东一郎和美国标准局的贝兹利(Norman Bazley)完成了有关氦原子最低能阶的计算,在可观测的精确度,即千万分之一以内,与实验值相符。很显然在这个案例中,物理学家从这些方程中「得到」我们并没有放进方程式的东西。
同样的事也真确发生在「复杂光谱」,亦即较重原子光谱的定性特征上。在此我要追忆我和约当的一次谈话。当时他告诉我,在光谱的定性特征推导出来后,如果由量子力学理论导出的规则跟由实证研究建立起来的规则不一致,这就提供了在矩阵力学框架内进行最后一次修正的机会。换句话说,约当觉得,要是在氦原子理论中出现意料之外的不一致,那我们至少在短期内将无能为力。这个理论当时是凯尔纳(Georg W. Kellner)和希勒罗斯(Egil Hilleraas)发展出来的。它的数学形式非常清晰且不可变更,如果上面提到的氦原子的奇迹未发生,那就真的会出现危机。毫无疑问,即使真的发生这种情形,物理学终究能以某种方式克服危机。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总有类似氦原子这样的奇迹一再重现,就不会有今天的物理学了。氦原子的情况也许是初等量子力学发展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奇迹,但它绝不是唯一的一个。其实在我来看,只要我们愿意去发掘,类似的奇迹要多少有多少。无论如何,量子力学具有许多几乎同样惊人的成功事例,这让我们确信它是─我们所谓的——正确的。
最后一个例子是量子电动力学,或者说兰姆位移(Lamb shift)理论。话说牛顿的重力理论与经验有着明显的牵连,然而经验却只有透过海森堡的处理方式化成精炼或改善的形式后,才能进入矩阵力学的表述体系。相较下,兰姆位移量子理论则根本是纯粹的数学理论,它由贝特(Hans Bethe)发想并经史温格(Julian Schwinger)所建立。实验唯一的直接贡献在于显示可测量效应的存在。实验与理论计算相符的程度优于千分之一。
与上述三者相类似的例子是无穷无尽的,但这三个例子应足以说明自然律中数学表述的适切性与精确性;在因为可操作而被选择的概念范围内,「自然律」有着几近神奇的准确性,但这仅在严格限制的范围之内。我提议把由上述实例所阐明的现象称为知识论的经验律(empirical law of epistemology)。它与物理学理论的不变性原理一起,构成这些理论不可或缺的基础。如果没有不变性原理,物理学理论就没有事实基础;如果知识论的经验律不正确,做研究时我们将缺乏情感上所需的鼓励和自信,而「自然律」也就不可能被成功探索出来。我与萨克斯(R. G. Sachs)博士讨论过知识论的经验律,他将这条定律称为理论物理学家的信条,这种说法显然正确。然而,他所谓的我们的信条都有充分的实例为证─例证远远不止上述三个。
物理学理论的唯一性
上述观察的经验本质在我看来是不证自明的。它当然不是「思想的要件」,我们应该毋需指出,它仅仅适用于我们对物理世界知识的极小一部分。如果位置本身或速度不存在简单的数学算式,却认定位置的二阶导数这种类似算式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这种想法当然很荒谬。因此,人们竟然可以视为理所当然的收下这份包含在知识论经验律中的神奇礼物,这一点确实令人惊奇。先前提到人类心灵能将上千个论证连结起来而仍然保持「正确」的能力,也是类似的天赐之礼。
任何经验律都会令人不安的一点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应用限制有多大。我们已经见到,有些周遭世界中的事件具备的规律性,可以用极为精确的数学概念来表述。另一方面,世界有些面向所关注的事物,我们并不相信有任何精确的规律存在。我们把这一切称为初始的条件。这裡自然浮现一个问题:不同的规律(亦即被发现的各种自然律)是否能融合成一致的单一整体,或至少趋近于这样的融合。又或者,也有可能总会有些自然律彼此之间根本找不到共通之处。目前来看的确如此,例如遗传学与与物理学的定律之间就没有共同点。甚至还有可能,有些自然律与另外一些自然律所蕴涵的意义互相冲突,但在各自的领域内都足够令人信服,以致我们不愿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我们也许会坦然接受这种事态,或是对于调和各理论之间的冲突逐渐失去兴趣。我们也许会放弃追寻「最终真理」——亦即,将自然界各方面所形成的小幅图像,融汇成一个具一致性的整体图景。
我们不妨用一个实例来说明这几种可能性。物理学中,我们现在有两个强大且重要的理论:量子现象的理论和相对论。这两种理论源自于互无交集的两组现象。相对论适用于宏观的物体如恒星。重合性事件(event of coincidence,也就是碰撞的终极分析)是相对论中的基本事件,它定义了时空中的一个点,或至少在相互碰撞的粒子无限小时会确定一个点。量子理论则来自微观世界,从它的观点,重合性事件或碰撞事件,即使发生在没有空间大小的粒子间,也不是基本的,更谈不上在时空中截然孤立。这两种理论运用了不同的数学概念:分别是四维的黎曼空间(Riemann space)和无穷维的希尔伯特空间。迄今为止两种理论尚未统一,即不存在一种数学表述,使得这两种理论是它的逼近。所有的物理学家都认为这两种理论的统合本质上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理论。尽管如此,也不难想像,我们可能始终找不到这两种理论的统合。这个例子说明了前面提到的两种可能性:统一或冲突,都是可以想见的。
为获得最终是哪种可能性脱颖而出的暗示,我们可以假装自己比现在更无知一些,假想我们的知识尚不及目前实际的水准。如果我们在这个较低的智力水准上能使这两种理论融为一体,我们就有自信在实际的智力水准上能找到这种融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较低的知识水准上得到了相互矛盾的理论,那麽我们就不能排除,这两种理论可能会永远相互冲突。知识和独创性的层级是一个连续的变数,这种连续变数相对较小的变动,不太可能把不一致的世界图像变为一致的【注:本段是在极大的犹豫之下写出。笔者相信在知识论的讨论上,我们最好放弃人类智力水准在绝对标尺上具有独一无二地位的想法。在某些情况下,去考量处于其他物种智力水准时可获得的知识,甚至也会是有用的。然而,笔者也明白,我在本文行文理路下的思考仍过于简略,所做的批判性评估还不足够,因而还不太可靠】。
若由此观点考量,我们明知有误的某些理论却给出了极为准确的结果,这会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假如我们略微无知些,则这些「错的」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群组,在我们看来已多到足够「证明」它们是正确的了。不过,这些理论之所以被我们认为是「错的」,正因为是分析到最后,它们与范围更全面的图像相牴牾。如果足够多的这种错误理论被发现出来,则必定会证实它们彼此矛盾。同理,某些被我们认为已经有够多的数据吻合足以「证明」为真的理论,也可能因为会和一个更完整、但我们还无力去发现的理论相牴牾,因而是错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一旦理论的数目超过某一程度,理论涵盖了足够多组的现象,我们就将看到理论之间彼此冲突。对照上述理论物理学家的信条,这不啻是理论家的噩梦。
让我们看看几个「错误」理论的例子,我们着眼于它们虽然有错,但却能准确描述几类现象。由于某种善良的动机,人们可以忽略这些例子提到的某些证据。波尔早年关于原子的开拓性想法所获得的成功,与托勒密的周转圆(epicycle)概念一样,是相当狭隘的。我们目前所处的制高点,让我们能精确描述这些比较原始的理论所描述的所有现象。而对于所谓的自由电子理论(free-electron theory),情况则大不相同。它极为精确地描述了金属、半导体和绝缘体的许多性质,甚至可说是大多数性质。尤其是,它解释了绝缘体电阻可以特别大,达到金属电阻的1026倍这一现象,这是根据「真实理论」无法恰当理解的。事实上,在自由电子理论预测绝缘体电阻值可以高达无穷大的实验环境里,没有实验证据表明绝缘体的电阻并不是无穷大。尽管如此,我们相信自由电子理论只是一种粗糙的逼近,应该被一种能更精确描述所有固体的理论来取代。
如果站在我们真正的制高点来看,自由电子理论所造成的局面很令人困扰,但它不像是在预告将出现无法克服的矛盾处境。自由电子理论反倒指出一些疑问,提醒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因为理论和实验的数值一致就相信理论的正确性。我们早已熟习这样的疑问。假如有一天,我们能建立一种关于意识或生物学现象的理论,并且这理论能像我们现在关于物理世界的理论一样一致和令人信服,则将出现更困难且更令人困惑的局面。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以及关于基因的后续研究,也许会成为生物学中这种理论的起点。并且我们很可能可找到一种抽象的论证,指出这样一种理论与公认的物理学原理有冲突。这种论证可能深具抽象的性质,使得我们不可能用实验来化解这个冲突,以确定该接受哪一个理论。这样的状况对于我们继续相信我们的理论,以及信赖我们所建立的概念的真实性,都会是莫大的考验。它将给追求我所谓「终极真理」的努力,罩上深深的挫折感。这种局面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理论为什么会那么管用。因此,它们的精确性并不能证明它们的正确与一致性。坦白说,如果能让目前的遗传学定律和物理学定律相较量,笔者相信将会出现类似上述场景的局面。
最后,让我们用较愉快的语调来结束本文吧。数学语言在表述自然律时的适当性是一项奇迹,它是我们既不理解也不配拥有的奇妙天赐。我们应当感激,也希望它在未来的研究中仍然有效。而且不论是好是坏,当我们尽情拓展知识领域时,即使会令我们困惑,也依旧成立。
笔者希望在此向以下各位致谢:博兰尼(Michael Polanyi)博士,笔者多年前于知识论方面深受其思想泽被;巴格曼(Valentine Bargmann),他的善意批评对本文的明晰度俾益极大。此外也非常感谢西蒙尼(Abner Shimony)检阅本文,并告知普尔斯的论文。
原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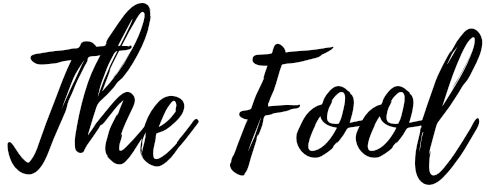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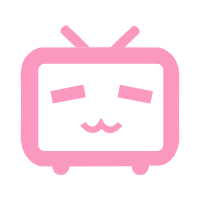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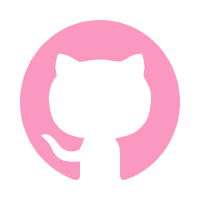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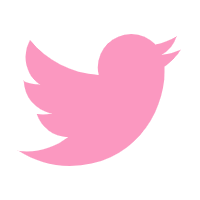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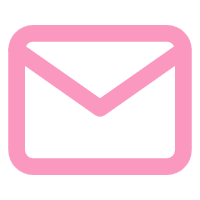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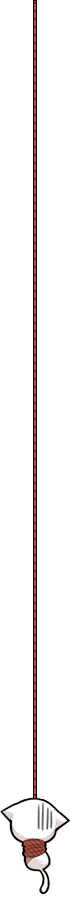
Comments NOTHING